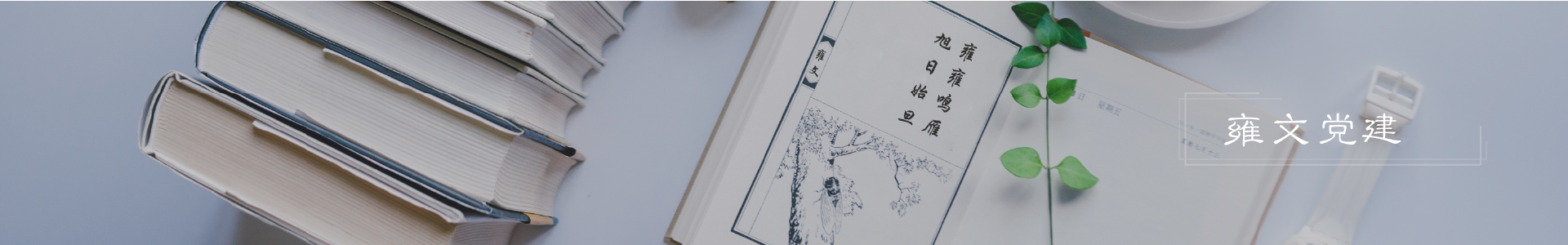
前言
不少客户面临手持胜诉判决但因被执行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被“终本”后,债权仍无法得到有效清偿的困境,救济路径一般为:一、执行追加;二、另行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诉讼;三、申请公司破产。本篇围绕救济路径二另行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依托真实案例,就裁判要点、法院审理思路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案件管辖
股东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之诉,属于侵权纠纷类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规定,债权人(原告)住所地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对该类案件具有管辖权。
问题产生:如原、被告住所地均不在A市,仅第三人公司住所地为A市,那么以公司住所地A市作为侵权行为实施地确定管辖法院,是否可行?答案是否定的。
二、裁判思路及典型案例
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九民纪要》第6条明确了股东出资义务可加速到期的两种例外情形:一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二是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虽然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在判决书中进行援引,但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可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考量和说理,现分别针对上述两款规定涉及的司法判例进行探讨。
1、如何适用《九民纪要》第六条第一款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目前司法实践中裁判思路:该情形实质上是需要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具体是指符合《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标的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暂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已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应认定为已具备破产原因,在没有证据证明标的公司申请破产的情况下,标的公司的股东不应再享有期限利益,即应履行其应尽义务,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相关司法判例:(2021)京03民终5147号,本院认为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第四条规定。 本案中嘉天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暂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已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应认定为已具备破产原因,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张小猛主张嘉天公司不具备破产原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在嘉天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调解书所确定债务的情况下,张小猛、孙明杰的出资期限虽未届满,但其作为嘉天公司的股东,有应缴而未缴纳的出资,属于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即应履行其应尽义务,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伯尔明公司要求张小猛、孙明杰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2、实践中遇到的特殊情形,关于历史股东是否承担责任问题。
为逃避补充赔偿责任,部分未实缴的股东在出资义务到期前转让股权,通过此方式逃避其应当承担的债务,因此个案中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原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债权人该如何救济?
(1)问题的产生
《公司法解释(三)》制定于公司资本认缴制改革之前,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以注册资本实缴制为背景,与《九民纪要》在资本认缴制背景下明确的“股东享有的期限利益”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对未实缴出资股权转让后的责任归属问题仍属于立法空白。
(2)目前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思路
一般情况下,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不应认定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构成《〈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或者存在一方欺诈、故意隐瞒事实等特定情形,则该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出资加速到期的补充清偿责任。
但考虑到股东的出资是法定义务和强制责任,在出资期限届满前将股权转让,仅仅是让渡了自己的合同权利,履行出资的合同义务并不会当然随着股权的转让而转移,如果在认缴期限届满前,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的,未经已有债权人同意或未对已有债权落实清偿方案的情况下,在满足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律要件时,仍要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股东转让出资早于公司债务形成时间的,公司债务与该股东并无关联性,若仍要求该股东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公平。
历史股东不承担责任的司法判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230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193号
历史股东承担责任的司法判例:(2021)京03民终15010号,本院认为部分:本案中从债务形成时间、股权转让时间上看,虽然叶庭浒出资时间尚未到期,但涉案债务在叶庭浒转让股权之前形成,而叶庭浒在上述债务形成期间,并未向门章公司进行任何出资,在债务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后,也未积极履行债务,叶庭浒在明知门章公司拖欠白麟债务且未履行出资义务,以及客观上存在执行程序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门章公司69%的股权以股权抵扣借款方式(18万元)转让给胡晓东,其滥用股东权利逃避股东责任的意图明显,已损害了作为门章公司债权人白麟的合法权益,故白麟申请追加叶庭浒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公司资本充实和维持的规定精神。
3、如何适用《九民纪要》第六条第二款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该条款存在争议的部分是“公司债务产生”的时间节点,是双方签订合同之时,还是一方已经履行完毕主要合同义务时?是合同约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时,还是法院作出生效裁判时?经查找司法判例,暂未在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案件中找到同类判例,但在减资纠纷案件中找到存在同样问题的判例,可供参考。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思路:
《九民纪要》将加速到期的适用条件缩在“债务产生后”,旨在审查债务人股东有无明知债务存在,却恶意延长出资期限的情形。当债务人及股东对债务有可预见性、应当知晓的情况下,应认为债权人已经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之时为债权债务形成之时,因为在一方履行完毕主要合同义务后,另一方应当对债权产生以及还款期限有可预见性。例如:借款合同,在一方履行完支付借款义务时,债权债务关系即产生,而无需苛求履行期限届满之时;同理,当债权人的或然债权有转化为现实债权的可能性,即债务人及股东对该债务具有可预见性,应当知晓,则债权债务关系在签订合同时即存在。例如:因为合同是债发生的原因,故买卖合同签订之日,即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之时,至于债权尚未到期或者债权数额尚未明确,均不影响债权人主张权利。相关司法判例:(2020)沪民再28号、(2019)沪02民终11793号。
反之,如债权并非合同一经签署即发生,则应具体审查债权的形成时间,债权债务形成的时间点仍要结合债权债务形成的具体原因判断,相关司法判例:(2019)苏0402民初920号,法院认为部分:在签署协议和交付保证金时银行对担保公司并未直接享有债权,双方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只要银行按约履行监管义务,不可能形成本案债务。担保公司对银行债务形成的条件,是银行不能按协议要求进行监管,擅自为担保公司办理解付保证金,造成资金流失,致使工程建设单位无法收回担保金。因此担保公司股东在2014年11月延长出资期限时,案涉债务尚未形成,担保公司作出延长出资期限至2029年11月1日的决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股东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
三、结语
《九民纪要》对于“股东应否加速到期”的问题已作出突破性的解释,因此,当债权人执行债务人终本后,可首先审查股东出资是否到位,进而要求股东以未出资金额为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种诉讼策略可以更加高效、经济的维护个体债权人的利益,成功实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